为什么明明是葬礼,可是在吃席的时候,人们还是有说有笑?
因为我很会讲笑话。
我奶奶去世的时候,家里人在老家搞了次酒席,大概十几桌,都在院儿里。
我记得那天很忙,母亲和其他亲戚在厨房帮做菜师傅倒腾锅碗瓢盆,父亲则在门口迎接那些过来吃席的客人,我在屋里躺着玩手机。
奶奶呢,奶奶躺在隔壁屋。
总之大家各有各的事儿,死亡那也算一种事。
其实当天来的人并不多,几乎都是一些父老乡亲,和父亲单位的熟人。
但这已经是这间宅子最热闹的一天了,难得的,门口停了好些个轿车,配上鞭炮声响,有种在过年的奇妙感。
我记得是十一点左右开的席,这个时间刚刚好,不至于让那些久坐的老人们,嗑瓜子磕到睡着。
父亲把我从屋里叫了出来,他对我不帮忙的懒散性子很是愤怒,但我想假设他知道我在看美女跳舞,他应该会更愤怒。
但他并不知道,在这个宅子里唯一能知道的,就是我奶奶的魂灵。
假设那真的存在。
我收起手机走到了院儿里,那天天色极暗,阴沉沉的总让人感觉身上有一层冷腻,时而吹来的风也把桌子上的瓜子弄得满地都是。
吵吵闹闹间,我随便找了一桌坐了下来。
旁边是几个穿着黑衣服的老人,坦白讲真不认识。随着精神病的日益加重,我时常会产生一种奇怪的感觉,那就是我总觉得这些老年人长的都很像。
真的很像,所以我认不出来。
但没关系,伪装正常是我的必修课,所以我也拿出一盒烟压在桌布上,然后边抽烟边嗑瓜子。
几个老人在我身边长嘘短叹,一会儿聊着哪个老伙计快死了,一会儿聊着带了多少礼钱,这些话题显然不是我能参与的,我的脑子里闪烁着刚刚屏幕里的雪白臀部。
怎么能长这么大呢,我皱着眉头又磕了一个瓜子儿。
忽然有人撞了下我的肩膀。
我偏过头,是我旁边的老人,他递给我一根烟,然后问我是不是一个人来吃酒的。
我想了想说不是,的确不是,因为白天吃剩下的,我知道晚上在家里我们还得再吃一遍。
你晓得素芬儿是囊个死的不,老人继续问我。
病死的,我心想原来奶奶叫这名儿。
哎,可惜了啊,人这辈子囊个说得清楚哦,老人发出了废话一般的感慨,他那张皱巴巴的老脸隐隐有些悲悯浮上。
当然,这并不影响他和我抢猪肘子吃。
我承认,转桌子我转不过他。
而一旦开始吃席,院子里的嘈杂声就散了不少,绝大多数人都晓得,他们来到这里唯一划算的事,不是掉多少眼泪,而是吃多少饭。
所以大家都吃的很卖力,我也一样。
恍惚间有了一种在猪槽面前排着队的感觉。
咀嚼声,碰杯声,窃窃私语声,孩童喊闹声,以及风声。
就像人世间的瓶瓶罐罐猛地被生死吹了个叮当乱响。
我本以为猪肘子终于该转到我这儿来了,但台上忽然就响起了我的名字。我有些迷茫地转过头,却看到灵台上的主持人正满怀期许地看着我,父亲同样也是。
于是我明白发生了什么。
他们叫我这个孙子上去讲两句。
某种荒诞感骤然间迸发了出发,我几乎都要笑出来了,只因这和小学舞台有着刹那间的重叠。
我站起身来,主持人拿着话筒说出了我这辈子都忘不了的话。
他说,大家掌声鼓励一下。
我低着头,从满嘴流油的猪肘子大爷背后走过去,在一片零碎的掌声里,我脑子里只回荡一个念头。
要不大家掌声鼓励一下奶奶复活吧。
可这终究只是念头,我还是漫步走到了灵台上,接过了主持人手里的话筒。我扭头看了下,奶奶的遗照正面带微笑躺在花圈中间,周遭的丧乐好像换了个曲子变得有点轻快,还有些许的哭声。
谁在哭呢,我看到二姑姑躲在柱子后面,捂着嘴掉眼泪。
真奇怪啊,我心想她不是恨奶奶吗。
但好像也很正常,这个家庭里的每个人都恨奶奶,但大家都忙活的像个痴心孝子,就连我都得上台两句了。
我拿着话筒,咽了口口水,然后看着台下。
没有几个人抬起头看我,而我甚至看到了有人已经在桌子下攥紧了黑色袋子。
一切依旧在照常继续,只是我仍然得扮演插曲。
荒诞感又一次涌上来,毕竟在死人的酒席上,让一个精神病来演讲,这真的不太符合道德伦理。
可是我必须要开腔了,我知道身后的父亲和主持人正在紧皱眉头,哪怕根本不会有人听,现在我也得说话了。
大家上午好,我发出了试探性的声响,就像婴儿啼哭。
没人在听。
今天我很荣幸站在这里,跟大家一起追忆我的奶奶,她叫啥名儿来着我怎么又忘了。
还是没人在听。
大家吃好喝好,奶奶一路走好,我仅用三句话就结束了全部。
而这一次,台下发出了剧烈的大笑声。
这真是个很好笑的笑话。
我抽了抽鼻子,没绷住打了个嗝儿,然后转身把话筒递给主持人,从父亲的身边走下台,无视了他脸上的铁青,开始接着转桌子。
猪肘子只剩一点了,旁边的大爷笑着说我讲的真好。
我也笑着说,你胃口真好。
好在这场荒诞的酒席结束的也很快,我承认那菜真的不好吃,而时间一晃来到了晚上,我依旧躺在屋里思考着雪白臀部的存在意义,亲戚们聚在院子外面烤火,旁边叠着白天的桌椅板凳。
我走到窗边,看着外面。
幺爸似乎有些不满,他低着头拿棍子倒腾着火堆,抱怨着今天不该只叫这么点人,可父亲蹬了他一眼,他便不敢继续说了。
没办法,我那骨子里怯弱的父亲,却有大男子主义的外壳。
在这个家庭里他是长子,他理所当然觉得他是所有人的父亲。
在爷爷和奶奶死后。
母亲忽然抬手擦了擦眼睛,她难得掉了次眼泪,并称奶奶还没有过什么好日子就走了,旁边几个姑姑叹着气安抚她,并异口同声地说,走了好,她走了,我们也解脱好多了。
我心想过去的确没什么好日子。
毕竟母亲过去和奶奶之间最多的交流,就是在屋里吵架时比谁摔得碗更多。
我忽然就不想再听了,于是我推开了奶奶的门,她的棺材还躺在里面呢,明儿个才会抬到山上去埋了。
我蹲在坑坑洼洼的地板上,把纸钱往铁碗里的火苗扔去。
我仿佛已经听到了某种声音,那是奶奶的尸体在缓慢腐烂,要不了多久,这具躯壳就会失去血肉,露出矮小的骸骨,然后在漫长的时间里蜷缩在泥土中。
就好像奶奶的死亡很缓慢,缓慢到她还没有完全消散。
而这之间的部分,我称之为魂灵。
她的魂灵就站在我身边,看着阳世的纸遁入火中成为灰烬。
噼里啪啦的鞭炮声猛地在窗外炸响,那不是我家的,但我想起了很多年前,那是真的很多年前。
我和表弟撅起屁股在院子里到处挖蚯蚓,长辈们聚在院子里拿了口大铁锅烤火,他们说说笑笑,而爷爷奶奶在厨房里忙忙碌碌,时而蹦出几句叫骂,让我俩小孩不要把新衣服弄脏了。
好像还贴了春联。
我的眼睛忽然有些发烫,于是我只能闭上眼睛。
生命的形式总是这样,人总是在死亡面前展露慈悲,而我这种精神病,却宁愿把这个家庭里的怨毒,仇恨,纷争,都看作是幻觉。
至少在这一夜。
谁恨谁,谁怨谁,谁巴不得谁死。
我都不必去想了。
奶奶的魂灵还僵站在我的身边,连同爷爷也叹息一声,靠着窗户抽着草烟。
哪怕我闭着眼睛,那假象的幻灭依旧在我心里重重叠叠,就因为我是这个家的孩子吗,还是因为我是祖祖辈辈养育出来最疯癫的怪胎。
这个家没有爱,这个家里没有谁爱谁。
在这里,没有拥有爱的人。
我也没有。
所以为什么要我给出一个答案呢。
猛地的风刹那吹开老旧的窗框,一声又一声的幻听在院里响起,好多人在喊着我的名字,过去的风雨被跨越百年的回响重现在今夜,四散的泥腥气把我的故乡重塑到当年。
我终于明白,过去所有的葬礼,那些人都没有真正死去。
我的所有祖祖辈辈,我的爷爷奶奶,他们的魂灵都还在这里。
是该做个了结了,何必再等呢。
何必真假呢。
我把头靠在冰凉的棺木上,缓缓睁开眼睛,任由泪水落了下来。
我爱你,奶奶,我小声地说。
一切都如此幻灭,但一切都在这里结束了。
风卷着那些魂灵的零散,悄悄把这扇门撞了个连环,那铁碗儿里的白烟,也终于兜兜转转,飘向了青天。
而这么多年后,该死的人,也终于都死了。
第二天清晨守完夜,推开门的时候,正碰见表弟,他笑着跟我说,怎么这副样子,像个菩萨一样。
我点了根烟,抬起头笑着说。
怎么,菩萨不能是精神病吗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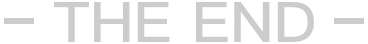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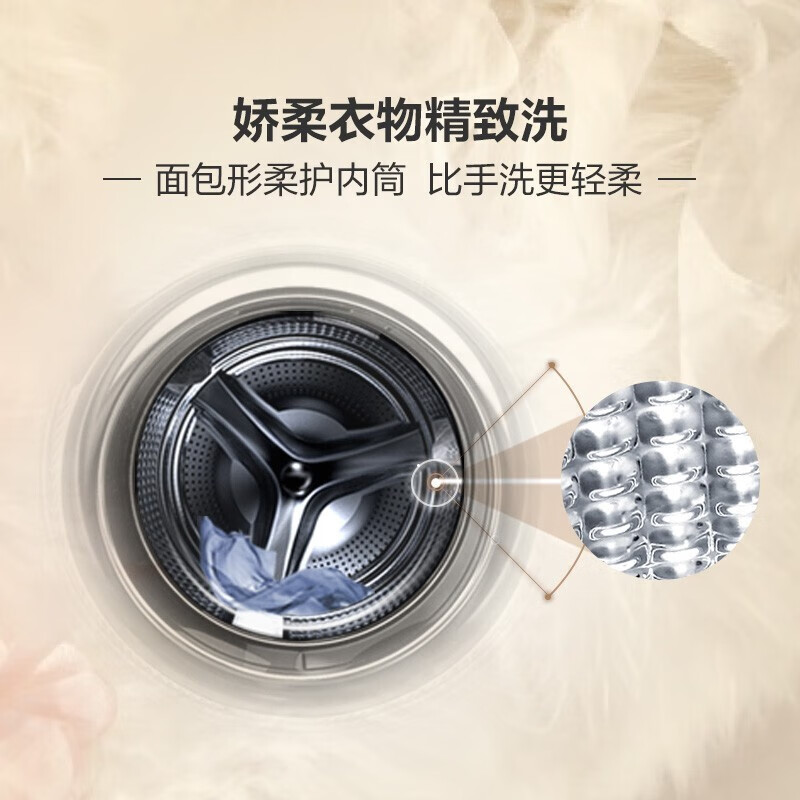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还没有任何评论,你来说两句吧